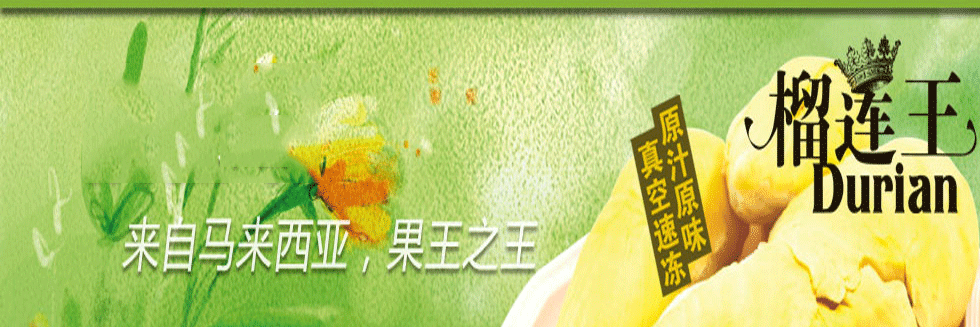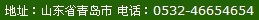|
我自小生在北大荒苦寒之地,只吃过桔子,没见过橘林。偶尔还吃过桔子罐头,通常是在感冒发烧的时候,算是生病的福利。从前物流不发达的年代,冬天能够吃到的桔子、苹果、梨都很小,比鸡蛋大不了多少。这些水果都是从外地运来的,我们本地出产的水果只有沙果、海棠、山楂、花红那么几种,个头儿就更小,都跟药房里卖的山楂丸差不多,也极少能留到冬天。所以,从语文课本中读到冰心的《小桔灯》,我就非常迷惑,得多大的桔子能够做成灯笼,里面放上蜡烛照人回家呢?冰心说她买的是几个“大红的桔子”,可我就是无法想象那桔子得有多大。许久以后,我知道这世上还有柚子、榴莲、波罗蜜那么大的水果,累累地悬挂在树上,真不由得要佩服那树的力气! 没见过橘林的我,却读不过不少咏橘的诗。诗里都赞叹橘的耐寒,说它经霜才更甘甜,这也叫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耐寒,为什么我们这里不种呢?古诗中称赞耐寒、耐霜雪的还有梅花,菊花,竹子,柏树,我们那里全没有,唯一有的是松树,倒有许多种:马尾松,落叶松,红松,油松。我费了好多时间和精力,才渐渐弄懂了那些南方诗人们所说的寒,跟我们这里的寒不一样,也渐渐弄懂了我们这里是在那中华文明的繁华盛景之外。住在黄河流域的人,以住在长江流域的人为南方人;住在长江流域的人,又以住在珠江流域的人为南方人;住在珠江流域的人,又以住在海南的人为南方人。而我们这里呢?把山海关以里的人,都称为南方人。原来一样是“南方”两个字,人们说的却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原来别人说的“寒”,跟我们说的“寒”也不一样啊!这种发现时时让我心惊——原来书里写的那些东西,跟我的实际观察和体验隔着十万八千里。可是,那与我隔了十万八千里的东西,依然在感动着我,滋养着我。 苏东坡有一首《浣溪沙》,是咏橘词,我很喜欢: 菊暗荷枯一夜霜, 新苞绿叶照林光。 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熏人惊半破, 清泉流齿怯初尝。 吴姬三日手犹香。 生在吴地的人,或许觉得这一字一句只是家常,可是对我来说整首词都很有异域风情。那“吴姬三日手犹香”尤其让我震动,仿佛那是个异族女子,在吃一种奇异的果子。其实生长在吴地的人,肯定觉得我这苦寒之地的人,才是少数民族女子——虽然我们都是汉人。我想我对于诗词的喜欢,也始终伴随着这种文化震惊,它总是再三再四地让我感觉到那种文化错位。 有一回,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带来一个大橘子给我,我立刻想起苏东坡那首《浣溪沙》,就和了他一首。边写边想,苏东坡是南方人啊,他到过的最北的地方是哪里呢?如果他见到一个来自松花江畔的我,他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文化震惊呢?他会有雅兴邀请我一同唱歌、填词、作诗吗?还是他只顾着催我讲那荒原上的家常:有一种巨大的萝卜叫拌倒驴,有一种鸟叫飞龙,有一种人参被称为绛珠草……我那首《浣溪沙·和东坡咏橘词》如下: 不在人前叹风霜, 惟存好意照流光。 十分颜色赏金黄。 未采当初碧树上, 非到熟时不敢尝。 遥思久后雪中香。 东坡可以写实,因为他见惯了橘林,橘子对他来说是寻常事,他咏的不是橘子,却是美人吃橘子。我只能写虚,因为我从未见过橘林,橘子于我终究有些神秘,所以我咏的不是写橘子,却是一种念想。 我至今仍然没见过中国南方的橘林。我倒是在美国的凤凰城,见过柠檬林。柠檬花开,香飘满城,倒叫我想起了茉莉花香的浓郁。从加利福尼亚去亚历桑那的路上,也曾远远望见两旁的橘林,才明白了为什么会有橘子郡的地名,可是依旧感觉隔膜——那不是我在中国古诗里读到过的橘林,诗中的世界于我是异域,驾车旅行过的世界于我依然是异域。萧红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才是我的乡土。 我刚才说过了,我们那里产的水果仅有几种,都是又小又酸,卖家最好的吆喝也不过是“酸甜”两个字。唯一大一点的水果,是柿子,确切说,是冻柿子——就这冻柿子,也是从关里运来的。我们那里的寒连柿子树也种禁不住。我到北京以后才见过新鲜的柿子;与小张认识以后,更是年年都想着去山里摘柿子:我喜欢大而熟甜的磨盘柿子,小张喜欢小而脆甜的漤柿子。我常常留几个柿子冻起来,夏天的时候拿出来用勺子挖着吃,称之为“天然冰淇淋”。那就是怀旧的时刻:从前在黑龙江,几乎每年三十儿的晚上,家家户户都要用凉水泡一盆冻柿子,等这盆凉水变成一个大冰坨,就可以敲开了,就从里面取出一个个已经化透的软柿子,咬破了,里面是金黄如蜜的汁肉。我们把这个解冻过程叫作“缓”,但是黑龙江人的读音叫作“欢”——我最喜欢这个过程,因为它给我的感觉确实是“欢”。 寒地不生橘,依旧留清欢。 谢谢 赞赏 人赞赏 中科白癜风公益活动北京最好的白癜风医院排名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ciguoyinyi.com/llyy/1179359.html |
当前位置: 榴莲_榴莲食品_榴莲营养 >寒地不生橘,依旧留清欢
时间:2017-12-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绿动中国改变世界自制环保酵素应用大全
- 下一篇文章: 101披萨加盟101披萨加盟费多少钱